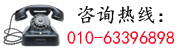摘 要:数字出版艺术唯有借助于张力,才能突出作品的艺术表现性和审美感染力。读者之所以能够直接感知并欣赏到数字出版艺术独有的艺术魅力,就在于其内在的智能动态张力性。一方面,数字出版艺术张力的形成,必须符合“矛盾排斥”“对立统一”之类的“二元对立”形式法则规律;另一方面,数字出版艺术张力的呈现则务必依赖于数字艺术特有的动态化图文声像表现方式、塑造手段,才能彰显其迷人的艺术魅力。
关键词:数字出版 艺术张力 智能动态 二元对立 图文声像
“张力”,表现为事物内部及其相互间相反方向的引力运动所形成的彼此对立、互为扩张的状态;是互相联系的动感视图和人的感知系统对知觉对象感知后所产生的知觉心理反映,因此,几乎所有门类的艺术无不借助于张力突出作品的艺术表现性和审美感染力。即是说,动态能够促成张力,继而张力引发审美感知。具有动态属性的数字出版艺术尤为如此。数字信息时代读者之所以能够直接感知数字出版的艺术张力,就在于动态化的图文声像、虚拟现实、遥在互动等智能形式,全然赋有这一艺术特点,其中,智能动态是形成张力现象最为关键的内在驱动力。
回溯历史,视觉艺术所涉及的张力问题,最初源自欧美文艺理论借用物理学领域惯用的“张力”语词,用以分析艺术中所存在的审美问题,其内涵有别于物理学意义上的“张力”现象。阿恩海姆认为:“在较为局限的知觉意义上说来,表现性的唯一基础就是张力。这就是说,表现性取决于我们在知觉某种特定的形象时所经验到的知觉力的基本性质——扩张和收缩、冲突和一致、上升和降落、前进和后退等等。”[1]很显然,在此所说的“表现性”,其实质就是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去解决艺术中的审美问题。对于数字出版艺术而言,“张力”是以事物矛盾双方“对立的紧张”[2]为基础,以智能动态要素为表现内容而获得的扩张力和独特的艺术魅力,同时,也反映出设计法则中,“二元对立”内涵向外延展的张力规律。
一、智能动态:数字出版艺术张力的本质体现
逐帧设计并连续播放“动态”图文声像,是导致数字出版艺术张力产生的关键,也是区别于传统纸媒“静态”出版物的本质体现。数字出版艺术所关联的“动态”张力现象,主要涉及两方面:一是直观的动画图文;二是静态画面中具有“动势”倾向的图文。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存在着同一视觉要素内部具有矛盾对抗力;或者不同视觉要素存有相互作用力。这些既抗争、又统一的受力现象,内含动态性质,彰显出“对外扩张”的张力属性。就“对立”的本质而言,是事物自身内部矛盾冲突所引发的对外扩张,自我对立消解,逐步统一的结果。然而,由其内而外促成的动态张力,不仅使得数字出版艺术显现出超常的动态特质,而且也赋予这一艺术形式赖以存在的数字媒体以新的审美含义。
客观现实中,数字出版艺术所蕴含的张力,主要体现在以数字出版媒体为信息传播平台的动态图形文字、虚拟现实图画场景、计算机影视动画中;体现在影像装置艺术、数字互动、沉浸式艺术、CG绘画艺术的笔墨神韵中……与此相对照的是,传统媒体时代,纸媒出版物所蕴含的艺术张力,必须通过静态文字视图的动势、方向、力场以及构图等创作手段来表现。读者感知张力,唯有凭借自身的经验累积与艺术学养,在场悠然品味,淡然悉心揣摩才能体会到。可是,到了数字出版时代,这类静态图形文字的笔墨力场、文图动势、编排方向等受益于计算机智能驱动,读者瞬间便可直观感受其特有的动感张力。
显而易见,计算机智能使得隐藏于图文、笔墨中静态的矛盾对抗力,用连续的动态画面呈现给读者,从而使之产生直观强烈的艺术张力,并能够促使读者直接感受之,而不必慢慢揣摩才能品味到。由此可以确信,智能动态是数字出版艺术张力的本质体现之一。
二、“二元对立”:促使数字出版艺术张力形成的内在因素
在所有种类的视觉艺术中,运用不同的“二元对立”表现手法去塑造创作命题是一个永恒不变的规律,数字出版艺术也不例外。以“矛盾排斥”“对立统一”规律为基础的“二元对立”,是促使数字出版艺术张力形成的内在因素。这类例子不胜枚举。诸如:静止与运动、真实与虚拟、节奏与无序、再现与表现、抽象与具象、平衡与倾斜、个性与共性、秩序与混乱、整体与局部;以及黑与白、冷与暖、疏与密、大与小、刚与柔、曲与直、形与神;似与不似等等……不一而足。就这类规律所具有的普适价值而言,任何一项法则仅是矛盾双方背反关系的抽象反映。假设将这一规律明确聚焦于某类艺术之上,抑或专指所属艺术的某一侧面,凡此种种,其价值所在,则是具体“二元对立”规律促成张力的现实反映。
例如,处在静止状态中的文字,仅反映出常规阅读情形下的信息传达。然而,一旦文字经过智能化的动态形变,字中所蕴藏的张力便以几何倍率增长向外传播,反映出“静”“动”“二元对立”能够形成对外扩展张力。此时,文字已不再仅仅作为传达信息的符号,或是表述观念的载体,而是从某个角度,幻化为直观拟态的“事”与“物”,在电子智能驱动下,单字、语词、行列、段落均可曲变为不同的动势造型。或表现“小桥流水”“飞流直下”,或描绘“崇山峻岭”“千山万壑”……“如诗如画”,“如泣如诉”。不管属于哪一类,但总能形象生动地表达文本的深刻内涵,彰显出数字出版的艺术张力。这也足以证明,“二元对立”内含“排斥”和“斗争”,经相互对抗、互为排斥后,向外扩张能够形成张力。
进一步而言,“二元对立”扩张,既可表现为不同事物两极点相互矛盾的“两极扩张”,也可表现为同一事物反向延展的“对立扩张”。无数相关的中继介质存于其极点间,而并非虚空无物,并存有一定量的“动能”以驱动两极点沿各自方向运动。“两极扩张”时反方向运动距离的远近,力的大小,直接影响张力的强、弱。格式塔心理学家经过科学试验证明,“二元对立”产生张力,与同一事物的中继点或两个相邻物体的间距密度有关。《艺术与视知觉》一书引言认为:“当两个圆面距离很近时,它们便互相吸引,而且看上去好像是不可分割的同一件事物。同样,我们还可以看到,当两个黑圆面之间的距离近到一定程度时,它们开始互相排斥。能够产生这些吸引作用和排斥作用的距离究竟多远,还要视黑色圆面和正方形的大小以及这两个圆面在正方形之内的位置而定。”[3]它表明,“二元对立”中的两极点间距“过密”,相互间能够产生相互吸引的“磁力”,而不能产生“张力”。“过疏”,间距太宽则二者间的排斥力减损,不足以形成有效的扩张力。把握好这个“度”是张力形成的关键。
在此,有理由确信,“二元对立”不仅能够促使、增进数字出版艺术张力的产生,而且也是引发张力形成的内在动力。
三、图文声像——表现数字出版独有的艺术张力
图文声像是构成数字出版艺术最为主要的信息成分,其表现方式、塑造手段、设计水准等能够直接表现数字出版独有的艺术张力,并关涉到艺术张力得以客观具体地反映。面对文本内容,设计师不仅需要协调设计构成要素与表现要旨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必须通盘综合考量构成内容,将版面文字、三维动画、声响音乐、虚拟现实、交互体验等,一应整合在某个合理的系统范围内以增进艺术表现力。设若设计师能够切合创意要求,全面理解并准确把握原著的思想内涵,使之具备独特的阅读浏览、审美欣赏功能,数字出版艺术必然能够形成超凡的欣赏魅力。不仅如此,设计师还必须运用数字出版自身特有的图文声像架构,准确把握设计格调,努力创作出新颖、独特的知觉审美形式,受众将因此享受到特有的阅读快意。若要实现此类目标,应遵循以下原则。
首先,设计师务必严格依照原著内容整体布局,对图文声像进行合理、确切的设计。只有在正确解读原文精神的前提下,设计师才能投入创作热情;采选设计角度,并以独特的图文声像形式诠释文化内容;彰显原文要旨;化育视觉美感。在知性动机的引导下,遴选确切的设计方案以满足纷繁驳杂的“学科类别”“消费对象”“时代年限”等不同方面的需要。即是说,设计方案应在知性分析与创意论证、草图筛选与构思优化主导下讨论通过。当然,设计师一定要有充裕的时间对原著精神进行悠闲、舒缓的思考,使信息传达,既生动、准确,又科学、逻辑。读者可从清晰的条理中,明了知觉信息相互间的内有关系,使图文声像所蕴含的张力,犹如不朽的诗作闪现出沁人心脾的艺术感染力。如斯艺术张力,既似诗人心灵智慧与造作工巧的集中体现;又好似诗人才思学养与知识储备的真实反映。
现实中,视屏界面上每一奇思妙想的点滴抒发,均会凝结成设计师心扉情感的结晶,并终将积聚成辛劳耕耘的收获。尽管张力委实隐藏于诗意般白色的版面中,不过,它却需要设计师穷尽才思,依据图文声像设计规律,将之开发挖掘出来,使超然的设计张力沿着创意轨迹,自然游走于页与页的空间链接转换上,以此创作出“笔落惊风雨”的设计佳作。
其次,选择确切的艺术形式,应符合数字出版的时代要求。并非所有的数字出版物都具有超然的张力,只有那些艺术形式与图文声像内容谐调吻合,且具有审美价值的设计构形才具备超然的张力。传统纸媒时代,面对卷帙浩繁的文学作品,设计师多依据文本内容、年代时间做相应的版面设计,确乎是把握信息传达张力的有效方式。简·奇措德(Jan Tschichold,1902—1974)是一位现代主义设计大师,“他把俄国构成主义和包豪斯的平面设计特点合在一起,发展出自己的平面设计风格来,他追求采用新的简单的字体,主张摒弃陈旧的中世纪字体,主张采用包豪斯式的无装饰线字体,采用包豪斯式的非对称版式编排方式”[4]。尽管奇措德是一位现代主义设计大师,但在针对不同的文本内容和设计对象时,却能揆情度理,见机而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不程式化、机械套用现代主义设计的条条框框。此举例所展现出的出版审美规律,虽为传统媒体时期的案例,但进入到了数字媒体时代,数字出版并未因传统纸媒读物日渐衰微,而否定这一设计规律,相反,却强调数字出版应基于传统精神,努力“拓其体、承其魂”,不断发扬光大。
最后,图文声像信息应以洗练、简洁的设计手法直观表达。无论是采用理性、逻辑,还是非理性、随机的艺术表现手法,将图文声像信息转化为设计心路,面对读者倾诉都必须干脆直接,简洁明了,“少即多”。对设计师来说,平滑洁净的数字媒体本身只是信息表达的载体。审美张力的呈现是通过数字屏幕,链接不同的视差页面,由读者体验、感悟而来。信息内爆时代,人们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去关注冗杂、繁琐的知觉形式。把握简练的图文声像等设计信息,不仅能帮助读者对原著进行直观、快速的理解,而且还能够使图文声像立马形成扩张力,迅疾在人群中加以传播。可以说,数字出版艺术张力的形成并非对图文声像资料的简单罗列和冗余堆砌,而是在符合时代需求的前提下,用简洁明了的设计手段,对信息构成给予文化上的分析与诠释,使形式与内容相互协调统一。可见,上述分析足以表明,拥有具体合理的图文声像构形方式与创意表达,能够现实反映数字出版的艺术张力。
要之,与其他门类的艺术一样,数字出版艺术必须借助于张力,才能突出作品的艺术表现性和审美感染力。数字出版艺术之所以有别于传统出版艺术,就在于其独有的智能动态性。智能驱动可以产生运动张力,使得读者能够直接感知并欣赏到数字出版艺术独有的艺术魅力。当然,数字出版艺术张力的形成,还必须遵循“矛盾排斥”“对立统一”等“二元对立”形式法则规律。只有当设计要素满足并符合“二元对立”形式法则的前提下,艺术张力才能得以形成。不仅如此,数字出版的艺术张力还必须运用特有的动态化图文声像表现方式、塑造手段,才能现实具体地反映其张力性。即是说,张力的产生不仅要符合“二元对立”规律,而且也是动态化图文声像审美方式具体化的反映。
参考文献
[1][3]鲁道夫·阿恩海姆. 艺术与视知觉[M]. 滕守尧,朱疆源,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640,12.
[2]金健人. 论文学的艺术张力[J]. 文艺理论研究,2001(3).
[4]王受之. 世界现代平面设计史[M]. 广州:新世纪出版社,1999:207.